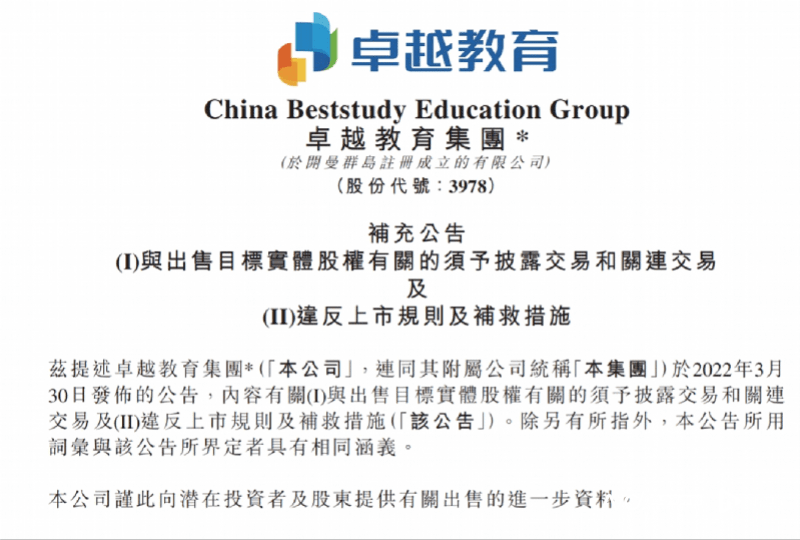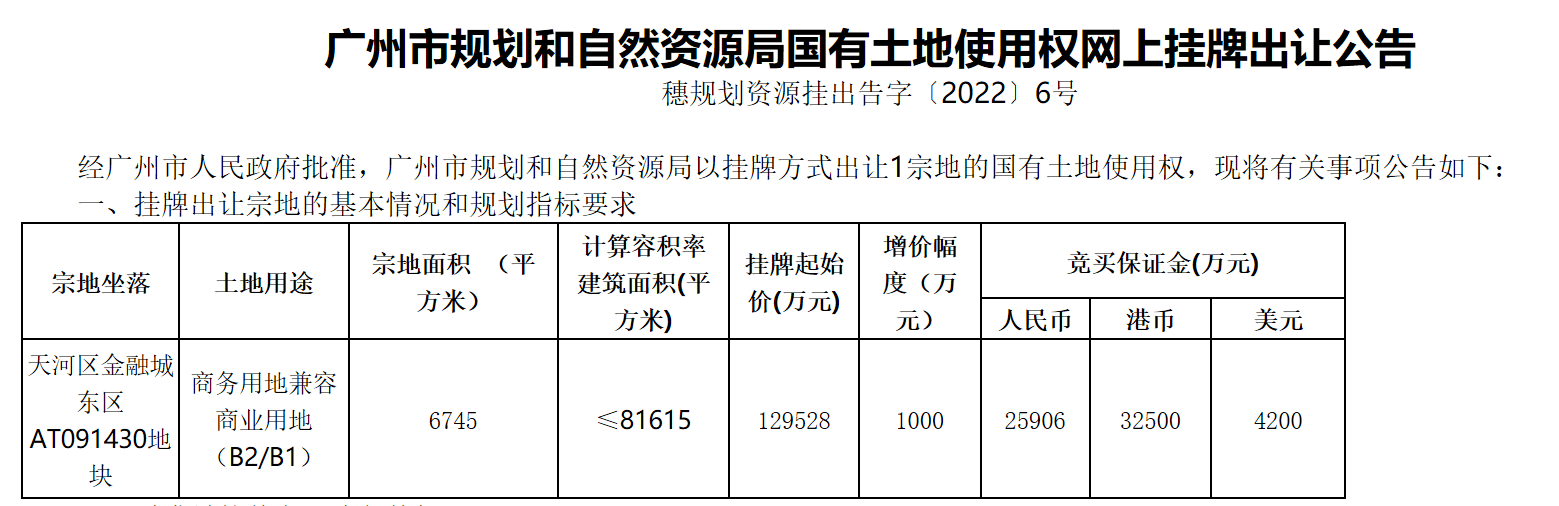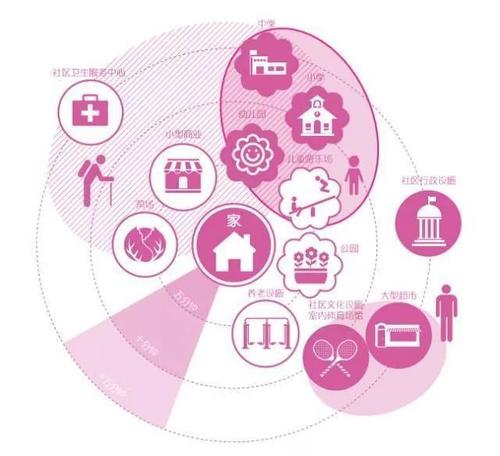引子
 (相关资料图)
(相关资料图)
本文试图围绕《漫长的季节》中的女性角色塑造来进行讨论。这部剧播出后,引发了各个面相的诸多讨论,而以类型搭载社会议题的创作方法也使它彰显出一种新的故事活力。因此,在此我们并非以性别问题的提出来讨伐创作者,或者要抹杀他们的贡献,该剧本身作为电视剧足够成功,这点是毋庸置疑的。
然而,我们依然要从性别文化的角度,来谈谈包括这一部而不限于这一部的诸多类型影视剧在性别塑造中所存在的,明显或隐秘的固化印象、偏见、以及性别憎恶。以及它们在剧中,是如何被表述成一种严密的,不能被挑战和颠破的创作惯例,该剧又是如何以文化习俗的逻辑来说服观众。
《漫长的季节》海报需要赎罪的丽茹在《漫长的季节》中,丽茹原本是桦钢医务所活泼可爱的年轻小护士,人人都愿意爱她;沈墨是桦医一年级清冷神秘的女大学生,人人都被她吸引。这两位女性的共同特征是漂亮,而在传统的中国类型化叙事系统中,年轻的漂亮女性往往最容易犯下性过错,因此是需要被惩罚和赎罪的典型。她们不仅仅是被渴求的,同时还是被憎恶的。事实上,丽茹和沈墨这两个女性角色,不断地被刻板化成“破鞋”和“祸水”的代表符号。在剧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对这种价值观的显性表达。
黄丽茹比如说,用一个似乎已经退出历史舞台的词——“破鞋”,在2023年的荧幕上讥讽和羞辱一位女性角色依然被视为是一个机灵的玩笑。1987年谢晋导演的《芙蓉镇》中,徐松子扮演的女干部李国香,被革命小将们推进大雨中,脖子上就被挂了一串破鞋以表羞辱。然而谢晋并非仅仅为了在最浅表的意义上羞辱李国香去使用这个比喻,而是利用这个场景点出了性作为历史创伤的复杂动因。在《漫长的季节》里,龚彪在得知了丽茹和厂长的不伦关系后,愤怒地打了厂长,之后走出会场整理着自己的绿色围巾和已经脱底了的“破鞋”,观众们顿时心领神会,仿佛这只是一个无伤大雅的玩笑。诚然,撇下这蹩脚的幽默感不提,我们真的能够通过故事,像了解其它几位男性角色一样,了解丽茹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女性吗?在桦钢行将解体之时,她为什么选择和厂长发展出这样的关系?她对待龚彪是有所利用吗?还是真心相许?她在想什么?她又为什么这么做?凡此种种,我们都很难得到答案。我们对她的印象总是不清晰的和片面的,我们只知道,在故事中她的魅力是邪恶的,她的心性是浅薄的,我们不关心她作为角色的生活,我们只会关注她在性道德上的过错。
因为,在这类故事中,作为女性的丽茹一点也不重要,重要的是丽茹有多放荡,就能显示出彪子有多高尚。丽茹这位女性的塑造,完全服从于龚彪的主体塑造。比如,在剧中为丽茹安排的惩罚性结局,便是让她承担由于性放纵而带来的意外怀孕以及随之而来的流产。一个年轻健康的女性在一次意外推搡之后必然会流产同时还会失去生育能力,这显然不是一个实际的或有医学根据的事实事件,而是失贞即失德,失德即遭报应的文化想象。在父系的文化结构中,“不能生育的女性”永远更让人唾弃,地位更低。
但这仍不够。流产,原本是完全属于女性自己的身心经验,可是这个最私密、最个人化的遭遇,也仍旧不能够属于她自己,而是首先被用来衬托龚彪的伟大。当龚彪坐在丽茹的床头,表达出对她“错误”的宽容,并表示依然愿意和她结婚时,我们首先想到的不是丽茹的身心感受和情感选择,而是龚彪“救风尘”式的浪漫,是他对抗整个既成文化价值判断的真心。至此,彪子的既愚且勇,和丽茹的既浪且贱完成了闭环表达。
经由这样的情节,女性的身体完完全全地成为服务于对不伦关系的审判,和对性放纵严厉惩罚的教具。这当然是通俗类型剧中,最无想象力的、老生常谈的一种道德训诫。
在故事18年后的时间线里,我们看到丽茹用了大半辈子来赎这子虚乌有的罪,直到再也忍受不下去选择离婚。而故事为她编排的,是让她离开龚彪投奔郝哥,以至于在龚彪驾车意外死亡之后,还有大量的观众认为,实际的情况是丽茹指使郝哥撞死了龚彪。和猜测是沈墨杀死了王阳一样,这种巨大的,不吝对角色报以最坏猜测的解读,仅仅来自于观众的误读吗?还是说,丽茹最终完成了从不值得被救的失贞女子,到出轨别的男人谋杀自己丈夫的全部戏码,映射出对我们这样的女性角色,充满憎恶和怀疑的价值观?
消失的沈墨
同样的性别文化价值认知,在故事的核心角色沈墨的塑造上,表现得同样明显。沈墨前半程是清纯的“圣女”,后半程是狠毒“恶女”。但这些都不重要,正如黑色电影中的“蛇蝎美人”也不重要一样,重要的总是那个为美人赴死的男性。况且,不同于标准的蛇蝎美人,她的魅力是借着柔弱,无辜以及纯洁而被大肆渲染的。丽茹主动地释放性魅力,沈墨则几乎一直是被动的,但是她的弱比丽茹的浪还更加吸引着周围的男性。这是因为在东亚的文化语境当中,女性的柔弱和清纯,根本上等同于最为男性所激赏的性感特征,被表达为最能够激发男性情欲的欲拒还休。
沈墨况且,她还必须首先处在受害者的位置,才有进入男性叙事的资格。大爷对沈墨的侵害是一切事端的肇起。这说明我们在想象一个较为复杂的女性角色的时候,性上面的创伤经历,总是会成为一个不需要加以审视的天然理由。女性步入故事的动机,要么仰仗男性施予的爱和恩慈,要么是由于男性施加的性创伤。然而,沈墨的命运也远非故事关注的重点。而是这样一个存在即错误的女性是如何一步步作死,最后害死了爱她的好男人们的。故事被设计为围绕着她展开,那么她的罪过就在于——她是她自己。她的存在本身被刻画成问题,成为各种男性犯罪的动因。剧中的恶人诸如大爷和港商,好人诸如王阳和傅卫军,无一例外地都围绕着她打转。无论她在哪里,是留在老家还是来到桦钢;无论她做什么,是去维多利亚弹琴还是乖乖读书;也无论她选择什么,是接受王阳的求爱还是拒绝港商的表白,都一定会(也必须)为她自己和周围的人招致更多的侵害与更大的麻烦。
特别是到了最后,不谈她杀人分尸的歹毒和算计谋划。只谈沈墨的基本人格刻画,她先是几乎毫不犹豫地牺牲掉自己唯一的亲人傅卫军,任由他给自己顶罪;其次当恋人王阳试图从和她这段施虐与受虐的爱情关系中解脱出来,拒绝和她一起逃跑时,沈墨几乎是以威胁自杀的方式,胁迫王阳跳入河中,并最终导致王阳因救她而丧命。这两个情节设计,再一次地,和丽茹的放荡衬托了龚彪超乎寻常的高贵一样,以沈墨的冷酷和恶毒衬托了王阳无与伦比的善良,和傅卫军令人心痛的牺牲。
而两位女性和同性的关系甚至比她们和异性的关系更加可悲,沈墨的大娘为虎作伥默许了大爷对她的性侵,丽茹自己的姐姐美素则鄙夷她的孟浪。在同龄的同性中,殷红对沈墨的嫉恨更是直接导致了自己被杀害后分尸。
美丽而年轻的女人中,丽茹不贞,殷红善妒,沈墨狠毒,不美而年老的女人如大娘和美素只剩下了懦弱和无用。这些反派特征,让她们在故事中的作用,和港商、大爷及厂长等表现出了更为令人不齿的卑劣品质的男性反派一样,终究是为了衬托主角团体的王家父子、龚彪、马德胜光辉正面人物的必要因素。
被杀的殷红与无用的美素
如果说,在男性统治的文化结构眼光中,“母亲”和“妓女”是两种基本的女性模式,那么在剧中,对应的便是作为母亲的美素,和人人唾弃的风尘女殷红。
罗美素除了作为王阳的母亲,美素身上还有一切刻板的,抽象的母亲要素:她慈爱体贴,但同时见识浅薄而软弱。大部分的时候她囿于厨房和毛线团,丈夫的大男子作风不会对她造成任何不快,一点点来自儿子的温情就足以让她满足。即便偶尔她会闪现出对生活的洞见,但世界上没有一个人会认真聆听她的建议。她的无价值,是王响18年后的闪回片段中永远只有对儿子王阳的念念不忘,而没有出现过一次对美素的怀念与追想,也没有一次表现对他们几十年夫妻生活的丁点怀恋。我们当然会觉得她可怜,但也仅仅是可怜。王阳死后,她随即毫无悬念地自我了断,原因不外乎,一个软弱的母亲必须塑造为始终为他人而活。
殷红而在剧中遇害的殷红,在剧情后半段草草出场,其作用在于顶替女大学生沈墨而被快速处理掉。这非常像张艺谋在《金陵十三钗》中设置的,以风尘女的命换学生的命的价值排序法,沈墨们在父系文化的价值排位中,依然高于以性谋生的殷红们,所以,风尘女们必须死。这位终极受害者,代表着无论中外;无论从开膛手杰克的年代,一直延续到21世纪的《杀人回忆》,在无数的犯罪类型故事中,一次又一次地被强暴、被杀死、被分尸,被社会枭以极刑的底层失足女性们。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在故事中,总是她们?总是这些以身体谋生的女性们,在生命秩序上成为戾气与暴力的终极承接者?甚至更糟糕的是,在《漫长的季节》中,她还在道德秩序上被表达为罪有应得。
好作品应该如实呈现时代的偏见吗?
即便有例证其上的种种,我们似乎总可以说,一个作品不过是如实地反映当时的社会面貌。作品中对女性角色的处理,不仅不是作品的缺陷,恰恰是它反映社会现实的精准之处。而我们今天用性别主义的方式去追究它的文化责任,根本就是对作品无事生非式的不宽容。
但,果真如此吗?
如果说,我们认可《漫长的季节》作为一部好的作品,那么我们就需要意识到它的好是作为一部标准的男性成长故事。整部剧在时间结构上的变形——一年四季之中的其它三个季节被压缩,剩下的一个季节则被无限拉长。季节在这里,是作为无限时间牢笼的隐喻而存在的。这个时间牢笼,才是需要成长的男性们亟需破除的真正对象。
即便是18年后的中年人主角团,整个故事线依旧是遵照着⻘春成长故事的模型。这“最后的夏天”或者“漫长的秋季”,既是文学意义上的季节符号,也是集体潜意识中共通的时间符码。在这样的季节里,通常是男人们被毕业,分离,茫然等选择和焦躁的情欲轮番教育,主动或被迫经历心理上的痛苦。最后和过去彻底告别,以此来完成精神上的断代,“我”自此将迈入真正的世界。
诚如卢卡斯在拍摄他日后风靡全球的,一群中古武士在宇宙里拿着光剑劈来劈去的《星球大战》之前,他真正意义上的第一部长片处女作《美国风情画》里所描述的故事主题——关于一群男孩如何成长。《美国风情画》的片尾打出的字幕交代,在不远的未来,此刻的年轻人们,或则丧命于无意义的追车,或阵亡于越南战场。于是,一个漫长夏夜中发生的日常琐事,才让个体的命运和时代之间产生了共鸣和交集。
《美国风情画》剧照而《漫长的季节》的导演辛爽所描绘的这幅“东北风情画”,将一个夏夜扩展到了一个秋季,也将男人们走入世界的时间,延宕了整整18年。男主角王响在下岗来临之前,对桦钢的爱诚如从未脱离母腹的幼儿的爱,这不仅仅是王响的问题,而是整整一代人在面对集体和个人关系的巨变时,在心理上未能成功分化的心理危机。于是在故事的前半段,我们看到,即便王响娶妻生子,人生过半,但还如同孩童一样幼稚,盲目地信任着桦钢这个早已从内部溃烂的母体。在王阳这位不愿意继承父亲精神生命的儿子死后,旧的王响人格才随之崩坏、离散死去,他才有机会逐渐走向人格的成熟,从而“向前走,别回头”。
表面上的悬案不过是故事的障眼法,故事真正的意图,是通过讲述王响的遭遇与成长,消弭“下岗”即意味着被“大家长”所抛弃的背叛与死亡体验的痛苦,试图重新整合出新的生活意义。这既是通俗类型作品的题中应有之意,也是它男性中心叙事再明显不过的特征。
王响然而,也正是因为我们无意识地接收了如此之多的男性成长类型故事,我们也完全习惯了对性别刻板认知习而不察的搬用,这让我们甚至很难发现它当中掩藏的问题。这部作品真的揭示出了我们生活中的真实吗?它创造的人物,是为我们带来了更为丰沛的视角,还是一再地强化了我们原本就充满偏见的认知?是不是在今天这个时代,我们还需要一而再,再而三地体察、认可和接受,属于90年代性别观的“就是如此”,以及将未来构造成一成不变的“理应如此”?还是那句话,“重要的不是神话讲述的年代,而是讲述神话的年代”。既然我们不是在90年代拍90年代的故事,而是选择了在今天讲述来自90年代的故事,那么我们真的能够以“从来如此”为借口,逃避作为今天的创作者,今天的观众,对着充满偏见和诋辱的性别观念所需要承担的文化责任吗?
也正是因为,一直到今天,围绕着我们的现实依然没有实质性的改变,这些观念在剧中的表达,才引发了我们的矛盾与痛苦之感。我们需要意识到日常生活里那些习而不察的文化范式,在何种程度上影响着我们所有人,从创作者到观众的认知,解构着我们的行为模式,乃至影响到我们与他人的关系。
也许有一天,在通俗作品中,我们能看到相对真实的性别表达,我们才会受到鼓舞,去展开性别之间真正的沟通和交流,也才有更深切地彼此理解的可能。
(本文来自澎湃新闻,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